
美国迄今贡献的最为非凡的结合了才华和智慧的作品。——爱默生
惠特曼作为一个世界性诗人,作品的影响早已遍及全球。对这样一个创造了美国文学经典的人来说,我们对他的观感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所谓经典,也许就像卡尔维诺的说法,就是提起来人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去读的作品。惠特曼是否也难逃此定义?
假如有人希望通过一个人的作品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尽管大家的名单上会各有差异,相信惠特曼一定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位。
1819年5月31日,美国建国43年后,惠特曼在纽约长岛西山村诞生。他的啼哭宣告了惠特曼时代的来临,而美国也幸运地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诗人”和“国家歌手”。所谓“民族”与“国家”虽然是惠特曼一生歌吟的对象,却是难以概括他作品的两个名词。
惠特曼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兄弟姐妹众多,年幼的他只读了几年书,11岁便辍学,随即在一家律所做了勤杂工。过早的人世辛劳与庞杂的社会阅历——惠特曼先后做过各种学徒以及印刷厂排字工人、记者、编辑等工作,这些都对他日后形成朴素的平等民主观念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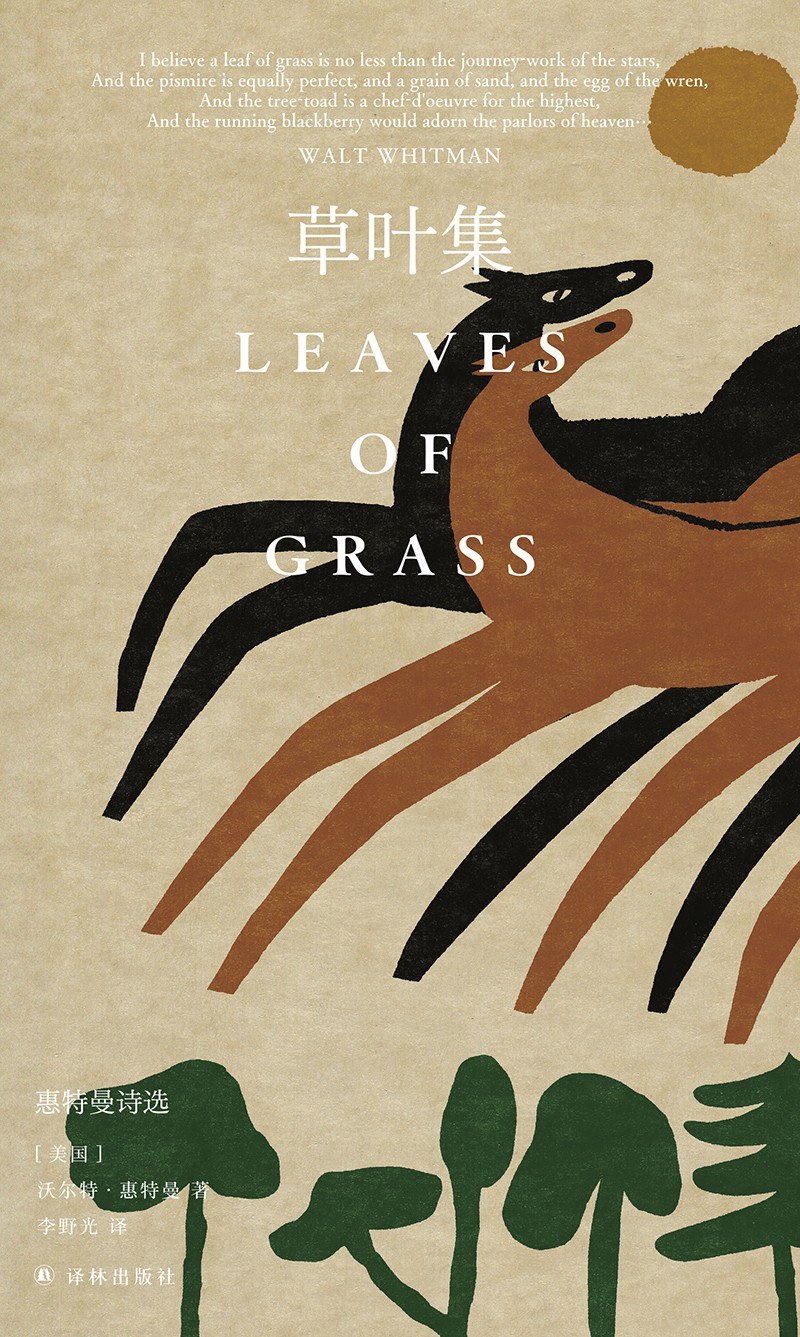
《草叶集》,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版
“先知”的拟神性声音
惠特曼的文学门徒众多,至今余响不绝。其中既有看起来与他气质迥异的诗人,如艾略特和史蒂文斯,也有他在拉丁美洲的真正传人聂鲁达。在他的一些诗句中,我们甚至能听到中国诗人海子的模仿与致敬。
他在名作《自我之歌》中这样写道:“我生在这里,我的父母生在这里,他们的父母也生在这里”,海子在《亚洲铜》里这样开篇:“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即便是一个不常阅读诗歌的读者,也能从这里看到某种血肉关系。
作家D·H劳伦斯评价惠特曼的时候说他是十九世纪之后诞生的最伟大的现代诗人,而诗人庞德则说:“我们还没有足够重视这个人高深莫测、从容不迫的艺术技巧,不是在细枝末节上,而是从大局上来看。”
的确,惠特曼的狂野激情以及粗犷的农民形象,看起来与忧郁深沉的现代主义大师们相去甚远。他作为美国诗歌源流的核心地位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也许,我们还要回到他自身的作品之中去探寻。
正如海明威(另一个惠特曼的文学门徒)更新了英国所代表的英语小说传统语言,惠特曼在诗歌中也发明了独属于美国的诗歌语言和迥异于英国的诗歌气质。在《自我之歌》中,他这样给自己描绘了一幅自画像:“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狂乱,肥壮,多欲,能吃,能喝,善于繁殖/不是感伤主义者,不凌驾于男人和女人之上,或远离他们,不谦恭也不放肆。”
初看这些诗句充满了狂野的悖论,极度膨胀的自我与谦逊的自我矛盾地和谐并行。他在很多作品中都展示出了某种自我中心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倾向,他时而化身上帝或上帝的门徒,时而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的语言混杂了天真与老迈,其中密布先知的拟神性声音。在未经修改的《自我之歌》手稿片段中,他是这样写的:“钉子无奈地穿透了我的手/我记得自己的十字架受难和血腥加冕”,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耶稣受难的形象,而在正式出版的《自我之歌》中,他也有这样的诗句:“我亲自量出耶和华的准确尺码”。在另一首《哥伦布的祈祷》中,他借助哥伦布的身份再次发出了这样的问话:“我说的是预言者的思想吗?或者我是在胡言乱语?/我听见一些新的语言的赞歌在向我招呼致意。”
这是毫无疑问的“先知”语言,哥伦布发现地理意义上的新大陆,而他,沃尔特·惠特曼则是用语言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创造的新语言也将更新美国文学的气质。

惠特曼
惠特曼在作品中故意消弭神与人的界限,这样的天真混沌特别适合他“创世者”和“谦卑万物”混杂的状态。还是在《自我之歌》中:“公牛和小虫从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颂赞/粪便和泥土有梦想不到的可敬之处/神异的东西算不了什么,我自己正等待着有一天也能成为神圣之物……我指着生命的块根起誓!我已经成为一个造物者”。在惠特曼看来,人与万物既是上帝的造物,也同样是自己的造物者,上帝潜行于万物之中,这便是他作品里随处可见的拟神性声音的由来。
惠特曼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是在一片蛮荒之中建立起新大陆自己的声音。他身上萨满巫师般的气质,让他分裂的自我形象更加动人,且具有无可争议的独创性。而含混不清的性取向与人神难分的写作视角,又让他的作品超越了某种性别和语言的界限。他太阳似的雄浑力量,尽管在他的门徒中偶有模拟,然而作为强力诗人的他实在罕有匹敌。
批评家布罗姆在其名作《西方正典》中如此评价惠特曼:“惠特曼的经典型在于他成功地永久改变了(不妨说是)美国的声音形象……爱默生自己已竭尽了全力,他也确实做得好,但他立即认识到这是他所预言过的诗人,一位文学的弥赛亚,而他自己则是为他服务的以利亚或施洗者约翰。”
惠特曼诗歌中的重复形式与复沓歌谣韵律
惠特曼是一位喜欢重复的诗人,阅读他的作品会发现他反复歌咏的对象或者说元素总是那么几样——自由与民主,灵魂与肉体——包罗宇宙,这种重复中的起伏变奏正是诗人不断修正自己思考的地方。正如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总是围绕着他所关心的几个主题,至于其他则是关于这些主题的变奏。
惠特曼同样如此。批评家海伦·文德勒认为:“重复是一种通过诗意的思考重塑感知的正式标志,独具匠心又富于想象力”。
在纪念林肯总统的诗集中,无论是《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还是电影《死亡诗社》中引用的那首《啊,船长!我的船长!》都有极为典型的表现。
“啊!在西方陨落的巨大星辰!/啊,夜的阴影——忧郁的、泪光闪烁的夜!/啊,巨星消逝了——啊,那遮没星星的一片阴沉!/啊,那抓住我这弱小者的残酷的双手——啊,我的无助的灵魂!/啊,那围绕在四周不愿解放我这灵魂的凶暴的乌云!”(《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
惠特曼诗歌中不仅会有重复的意象元素,还会有重复的歌唱形式,如上所示便是抒情形式的重复,某种充满音乐性的节奏韵律一再出现,他强调的是诗人强烈的情感以及便于吟诵的诗歌特质。
在《啊,船长!我的船长!》中,他这样写道:“啊。船长!我的船长!我们可怕的航程已经终了……啊,船长!我的船长!清起来听听这钟声”,这样的结构,应该说是偷师民谣中的“复沓”,为的是吟唱与传播的方便。
类似的写法,存在于惠特曼多数的作品之中。这位“不怎么优美雅致的,胡须满面,晒得黝黑,灰色脖子,难以亲近”的诗人,几乎歌唱过美国的方方面面,他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歌手。
他为美国各个州写诗,为总统、探险家写诗,也为一草一木山川河流写诗,他甚至“歌颂带电的肉体”——在此,我们清晰地辨认出聂鲁达与郭沫若的师承。
“我是个属于各种肤色和各个阶级、属于各种地位和宗教的人”,他如太阳般照耀万物,也像宇宙般吞吐万物,他身上诸多的矛盾统一在此后很难有别的诗人继承。
他膨胀的自我有如美国文化中极度张扬的个性,他谦卑宽宏的口吻又似美国多种族文化熔炉的兼容并蓄。他是美国精神的不朽旗手,他说“要以伟大的喉舌将美利坚征服。”(《欢乐之歌》)
他自视为“上帝忠实的儿子”,没有什么评论比得上他诗句中的自我指涉:“新发现的陆地和诞生的国家,你新生的美国/为了宏伟的目的,人类长久的见习期已经完满/你,世界的环绕已大功告成……最后一定会出现无愧于自己称号的诗人/上帝的忠诚儿子一定会唱着自己的歌向我们走近。”
在《神学院演说》中,爱默生认为耶稣“看见上帝化身为人,由此新生并出发去拥有他的世界”。至此,一个美丽的新大陆被发现与命名,一个伟大的诗歌国度也在惠特曼的笔下强力诞生。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